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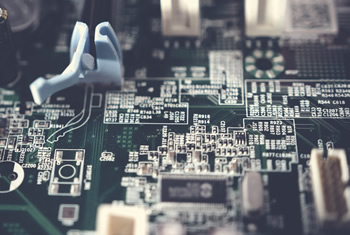
读了丁肇中先生的《应有格物致知精神》一文深有同感,认识到我们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确实有很多弊病,但对于丁先生对“格物致知”的理解我仍抱有疑问,因此就借这次机会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。
文章中说“真正”的格物致知是“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,并就此认为格物致知就是“我们所谓的实验”。韩维志在译评《大学》时就曾明确指出《大学》的原文缺少对“格物致知”的阐释,古人因此也做了诸多不同的见解,甚至是大理学家朱熹也曾专门对“格物致知”补缀了一篇论文。然而,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“格物致知”就是真正的“格物致知”,那么对儒学研究不深的丁先生如何可谓“真正”的“格物致知”呢?对此我实在无法认同。
而那勤于格物的阳明先生也恐怕是受冤了。丁先生认为他“格竹七日而不得正果”是因为他“把探究外界”误认为是探讨自己,并于后文说要“格竹”就应“栽种竹子,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,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”,这番话着实让人无语。我想丁先生大概是混淆了哲学和实践的概念。儒学无疑是一种哲学,而哲学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思想体现,与由外及内的实践完全不同。用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的话说,哲学是理论的理论,它高度抽象,与实践隔绝,它志在理解而非改变世界,而当其转化为实践时也就失去了其作为学术的学术品格。也就是说哲学本身就是要优先探索自身,然后才能推己及人的。那么这与“栽种”和“拿到显微镜下观察”又有何干呢?想来实在是可笑至极。